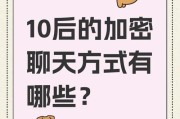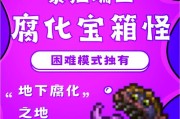多余者的自白:当"无用"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底色

"我不过是个多余的人。"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,划开了现代人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表皮,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真相。在这个崇尚效率、崇拜成功的时代,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一种难以名状却又刻骨铭心的存在危机——感觉自己是个"多余的人"。这种感受并非源于物质匮乏,而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;不是由于能力不足,而是价值体系的扭曲异化。当社会将人的价值简化为生产力与消费力时,那些无法或不愿融入这一逻辑的个体,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推向了"多余者"的孤独境地。
当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在资本的逻辑下,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、有尊严的存在,而是被分解为各种功能性的零件——生产者、消费者、纳税人、数据点。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警示我们,现代社会通过种种规训机制将人塑造成符合系统要求的"有用个体"。而那些无法适应这套游戏规则的人,则被系统性地边缘化。更可怕的是,这种异化已经内化为现代人的自我认知。我们开始用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:我能创造多少经济价值?我的社交账号有多少粉丝?我的存在对他人"有用"吗?当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尽如人意时,"多余感"便如影随形。
"多余的人"这一文学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深厚的传统。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·奥涅金到莱蒙托夫的毕巧林,再到屠格涅夫的罗亭,这些"多余的人"共同构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。他们通常出身贵族,受过良好教育,却对生活感到厌倦,无法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社会位置。赫尔岑曾这样描述:"他们聪明绝顶却一事无成,渴望行动却总是犹豫不决。"在当代语境下重读这些形象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,尽管时空变换,人类精神困境的本质却惊人地相似。今天在大城市写字楼里感到虚无的白领,与当年在俄国庄园里苦闷的贵族,在精神谱系上竟是一脉相承。
现代人的"多余感"有着更为复杂的成因。社交媒体的普及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悖论: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"连接",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。在Instagram和朋友圈的光鲜表象下,是无数个深夜刷屏时的空虚与自我怀疑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指出,当代社会已经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,人们不再被他人压迫,而是自我剥削,在"你可以"的鼓励下陷入无止境的自我优化焦虑。当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日益模糊,当成功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,那些无法达标的人便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——"我不够好"、"我不配存在"。
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解"多余感"提供了另一视角。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开篇便指出:"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自杀。"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继续,这相当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。萨特则更为直白:"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。"这种自由不是礼物,而是重负,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。在上帝已死的世界里,人必须独自面对存在的荒诞与无意义。这种觉醒带来的不是解放,而常常是更深的迷茫。当所有的意义都需要自我建构时,"多余感"便成为现代人无法逃避的精神境遇。
面对这种存在困境,我们能否找到救赎的可能?俄罗斯文学中的"多余的人"最终大多走向悲剧,但今天的我们或许有更多选择。首先需要认识到,"多余感"本身就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产物,不必为此过度自责。其次,重建价值体系至关重要——人的价值不应仅由生产力或社交资本决定。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"他者伦理",认为正是对他人的责任赋予了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在志愿工作、艺术创作、深度关系中,我们或许能找到超越功利逻辑的生命价值。最后,学会与"多余感"共处而非消灭它,承认这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,就像阴影是光明的必要补充。
在一个人人被期待成为"有用人才"的时代,或许更大的勇气就是允许自己偶尔"无用"。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写道:"负担越重,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,它就越真实存在。"那些让我们感到"多余"的瞬间,恰恰可能是我们最接近真实自我的时刻。当社会机器高速运转时,能够停下来质疑自己的位置,这种自觉已经是抵抗异化的开始。
多余者的伤悲不是软弱的表现,而是敏感的代价;不是失败的标志,而是觉醒的征兆。在这个意义上,每个感到自己"多余"的人,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质询着这个时代的价值迷思。他们的困惑与痛苦,恰恰照亮了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。当我们停止用"有用"或"无用"的二元标准评判存在本身时,或许能够发现: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生产了什么,而在于你如何体验;不在于你改变了世界,而在于你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。在这个被绩效和指标统治的时代,能够感受到"多余"的伤悲,或许正是我们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证明。
 富贵体育网
富贵体育网